清朝挨的打最多.那個年代朝臣吹的牛逼也最光芒耀眼。
在雷頤《曆史的進退:晚近舊事與集體記憶》一書裏,你能看到清臣讓人驚掉下巴的胡吹海侃。
A:鳥語不能學!天文不能學!機械物理不能學!
兩次鴉片戰爭被洋人狂扁,清廷卻隻有少數人覺醒,而覺醒的程度也很淺表,像總理衙門王大臣奕䜣,這個皇親貴胄,也隻是想起該讓國人學點外語,能跟洋人說上話,再學點算術曆法類基礎知識。但即便如此,還是遭到飽讀詩書的眾臣萬炮齊轟。
當年,總理衙門王大臣奕䜣等創辦了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同文館。
1866年底,奕䜣上奏,提出要招收“ 正途” 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想在重科舉的社會裏,提升下自然科學的地位。

尚有幾分覺悟的皇叔奕忻
如奕䜣所料,同文館擬添設天文算學館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消息傳出後,頑固派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樣跳將起來。
聽聽奕䜣與守舊派的大辯論,領略下守舊派頑愚與國人當年對維新派的群毆,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奕䜣說,中國人以“ 師法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他先說明為什麽不得不搞西學:”當今既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如不借 西人、
西法為先導,探求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結果必然徒費金錢,無實際效果。”
他知道當朝很多人以“師法西人”為恥,他說,不如人、挨打才該感到恥辱:“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
他試圖用近鄰日本來刺激國人:“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亦必有成……
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奕忻意思是,學習西方是為了“ 雪恥”, 拒絕學習,不如人才是真正的恥辱。
頑固派大將、管理戶部(即全國財政)的文淵閣大學士倭仁橫刀立馬,領頭圍剿洋務派,他遞上奏折——“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他認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不過是“一藝之末”,而士人學子奉夷人為師,所造就者不過是“術數之士”,那是國之大辱:“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夠起衰振弱的。”他振振有詞地說:目前世道衰微,禮崩樂壞,唯有依靠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員“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數年之後,“將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所以請求朝廷立罷此議。倭仁是公認的理學大師,言辭懇切,極具煽動性,在士大夫間形成一股反對學習西學的強勁力量。
對此,奕䜣等人上折反駁說,倭仁之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他們在沒有辦理洋務之前,也是如此見解,
但現在他們不敢像倭仁那樣一味“空言塞責,取譽天下”。他們認為,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講求機器製造之法、教練洋槍隊伍、派人出國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目前奏請開設天文算學館,實為製造輪船及各機器的基礎,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
居於弱勢的奕䜣等人都快杜鵑啼血了!
他們痛斥頑固派“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記吃不記打,光剩一張嘴。
頑固派最後亮出絕招,用天災人禍嚇唬朝廷。
候補直隸州知州楊廷熙通過都察院遞上《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折》,以“天象示警”來說事。他指說今年春季以來久旱不雨,疫癘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師中街談巷議,皆以為同文館之設,強詞奪理、師敵忘仇、禦夷失策所致”,認為總理衙門請求設立同文館是“不當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眾論”,“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
楊廷熙幾乎勒令清廷:為“杜亂萌而端風教,
弭天變而順人心”,必須“收回成命”,將同文館予以裁撤,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員報考天文算學館。
楊廷熙聲稱:中國欲求自強, 隻需要“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作忠義之氣於行間,盡教養之懷於民上”,則洋人雖眾,槍炮雖利,輪船雖多,
亦斷不敢不敢肆虐於中國。他強調西方國家乃中國之“敵國”與“世仇”,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就是“師事仇敵”,他認定“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即便“多才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振振有詞,滔滔不絕。
果然,在頑固派的圍剿之下,這洋學館果然沒什麽正經人報名,後來更沒幾人真正學成畢業,總理衙門王大臣奕䜣的同文館,等於被攪黃了。
守舊的臣民攪黃了“蠻夷之學”,成功地阻止了天朝與蠻夷的同化與共進,給大清留下的就隻有繼續挨打一條路了。按說,挨了打,該閉嘴了吧?恰恰相反,天朝培養出來的文士嘴硬無敵,他們竟能化腐朽為神奇,把挨打國辱說成天朝榮耀,而且言之成理,滔滔不絕——
B:世界早晚是我大清的!
中國從來以“天朝上國”自居,到後清幾乎年年挨打,卻從來不乏“理直氣壯”,朝臣眼裏,無所謂“中外關係”,都是天朝上國對狄夷的撫剿和統,“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用懷柔手段,遠近都能搞定。幾千年來,“柔遠”、“懷柔”一直是中國統治者馭外、安撫四方狄夷之術。後世帝王對“
九夷八蠻”(神州各民族兄弟)或撫或剿、或和或戰都統稱“柔遠”或“懷柔”,在前朝,這些曾經很有用,很好使,但到了近代,洋人堅船利炮麵前,還說這些已經是驢唇馬嘴,但“能臣”竟是能言之鑿鑿,說得滿朝雞血,幸福洋溢。
1879年,天朝一本《國朝柔遠記》,賣得洛陽紙貴,成為當年愛國主義的經典著作,書中,把挨打說成天朝賞賜,打造出阿Q的頂級豪華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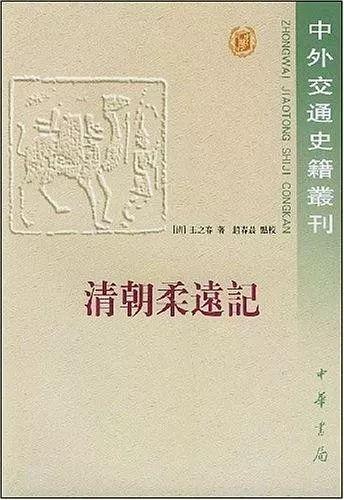
該大作作者王之春,曾為曾國藩、李鴻章幕僚,曆任山西、安徽、廣西巡撫,是清廷高幹,他以編年體形式綜述清代自順治元年(
1644)到同治十三年( 1874) 間中外交涉和與邊遠少數民族關係
,熬心費血,完成了這部“不朽”著作。據他說本意不過是“自己備忘之用,而未敢問世。”然而由於向他借閱者越來越多,應接不暇,於是決定刊刻發行。全書共十九卷,跨度二百三十年,
但筆墨重點在從道光十九年( 1839)至同治 十三年(1874)的三十五年,
這後三十五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意在說明,鴉片戰爭後這三十五年間的“ 柔遠” 遠勝於此前的一百九十五年。
按照王之春的說法:在前一百九十餘年間,我中華“天朝”對“外藩”的政策是,如果它對天朝俯首稱臣,自然優待;如果它氣焰囂張、不服“天朝”的管,“則罰滅之”,在理論上
,無論是優待還是罰滅,都可說是“柔遠”。
而十九世紀中後的三十餘年,殘酷的現實是,大清總在挨打,列強侵逼,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所有這些明明是被人蹂躪,如何能說是“
國朝”的“柔遠”呢?
不用愁,當年,有彭玉麟、 譚鈞培、衛榮光、俞樾、李元度名流,紛紛給王之春大作做“敘”,他們自有高談闊論,不由你不服。
彭玉麟為湘軍勇將,他聲言讀完這本書,“穆然仰見列祖神宗聲教”傳到全世界,不禁盛讚“蓋自文、武以後,柔遠之政未有若是之盡美盡善、
可以行久遠而無弊者”。自周文王、周武王之後,中國曆朝曆代的“柔遠之政”竟沒有如晚清“盡美盡善”者!
就是說,這段時間被揍得結實,所以“柔遠之政”看上去更美,正如魯迅說挨打之後“豔若桃花”。
原雲南巡撫的譚鈞培在“敘”中說早在康乾時期,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天”要合四海為一家的端倪了。也就是說,中國遭列強侵淩的實質是“天之欲合四海為一家”,康乾盛世時“天下承平”的中西交往隻是這種四海一家的開始,康熙、乾隆才剛剛有所覺察,而幾乎天天挨打的鹹豐時期卻是“天”要中國降服狄夷的正式過程。道光、鹹豐年間雖然列強不斷入侵,京師曾為英法聯軍攻克,皇家園林圓明園亦為其焚毀,但若對此作深刻細致的研究,這恰是上天賜給的由中國來同化世界的良機,他說,王之春這部“柔遠”記述的便是“四方”歸化“中國”的曆史,所以其意義不下於《左傳》。
而曾任江蘇巡撫的衛榮光則從“曆史”中尋找根據,認為今日的列強就是昔日《禹貢》、《周官》中所說的“
九夷八蠻”,仍是中國屬臣。在他的論述中,列強之所以要以堅船利炮翻山越嶺、跨洋過海一路打來,原來是為“我朝”聖主的道德、聲望折服,都是來接受指教,將要仿效中國“德政”,於是則四海一家,“如天君泰而百體從令”。列強,竟是為聽從“天朝”君王的命令而來!
專製高壓下的臣子,如同SM世界裏被虐爽了的M
,身受殘虐卻高唱頌歌,其實,這種景象從來沒有斷片兒,不信?看看東鄰的臣子是如何歌頌大將軍的!
俞樾是晚清著名學者,他認為《國朝柔遠記》問世意義深遠,讀後不禁歎服“天道”宏偉、覆蓋一切,“而我國家所以長駕遠馭、陶六合為一家者,其將在此乎!”他更是斷言當今世界分為五大洲即印證了中國上古的“大九州”之說,但推出上古的“大九州”並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說明在神農氏以前,世界/天下是由中國統治的。自神農以後,天下分裂,“中國”成了神州內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現在
,機會來啦!列強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就是為了使世界再恢複到神農氏以前,由中國統治“大九州”即全世界的狀態,中國君王將重為“大九州”之君。西方的“長技”隻是“末技”,
隻有中國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根本。所以,他極為樂觀地認為這部“ 柔遠記”便是世界重新由中國“大一統”的先兆。
厲害了,我的國!
曾入曾國藩幕、後任雲南按察使及貴州布政使等職的李元度寫道,“堯舜孔孟之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是萬世不變的。因此,中國現雖遭西方諸國侵略,但他們的文化價值觀不但不可能“奪吾堯舜孔孟之席”,恰恰相反,堯舜孔孟之教將在西方各國盛行,此時便是這一時代的開始。因為上古時代西方各國不通中國,又相去數萬裏,所以他們不知道有聖人,未能得到中國聖人的教誨。他們發明鐵路輪船,就是為了前來中國接受教誨。
李元度把洋人的特性概括為殘忍、機巧、強梁、陰險、狡猾、忘本、黷武、專利、奢侈、忌刻,這十大特性條條都深犯“天忌”。但是,天心仁愛,聖人有教無類,要把孝悌忠信從中國恩賜給這些毫無文化的“蠻貊”。今天西方列強侵華,恰是上天誘使他們進一圈套,他們為了通商得利都來到中國,於是“
漸近吾禮義之教,自然幡然大變其俗”,所以我們不必擔心西方的“教”將“奪吾堯舜孔孟之席”,結果必然是他們“幡然改從堯舜孔孟之教,然後不失乎人之性,而無犯造物之所忌”。他堅信:“吾知百年內外,盡地球九萬裏,皆當一道同風,盡遵聖教。‘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聖人無疑矣!”
經過這幫高師大德的演說,充滿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被淩虐出快感,反成了一部“國朝柔遠”的豐功偉業史,隻可惜,大師們欣欣然的大一統,天下一家,並沒有出現。僅僅過了二十多年,意淫王朝就轟然坍塌。後來,不是東方同化了西方,倒是西化日盛一日。
但直到今日,仍有人在做著東方大同的夢,更有人總愛把西方成果比附為祖上遺產,凡當世新事物,無一不源自我們祖上遺傳。
梁啟超曾用鄙夷的口吻形容那種試圖用孔學”招納“各類新學的方式: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雷頤說,如果去掉過於尖刻的“ 舞文賤儒”四字, 此番評析,對百年後的“ 新儒家”
也完全適用,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君不見,時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風正盛,更不乏以和諧、環保、自由、民主、法製、公平、正義、人權、市場經濟……一切現代價值來詮釋、比附儒學,論證所有這些價值、觀念儒學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學“返本開新”的“新儒”學者。若起梁氏於地下,麵對此情此景,他依然會果決地做出“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的斷罷。
C:你們去照實殺人,我隻要好名聲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偏狹冥頑的清朝廷臣挑唆狂熱子民,濫殺無辜,最後搞砸了鍋,讓國家和草民背鍋的經典範本。
因在祺祥政變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開發表議論,狂熱疾呼:設法激勵鄉紳,激勵眾民,賢者示以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沉其貨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則以查辦為詞以緩之,日久則以大吏不便盡治一省之民為詞以絕之……
若謂該酋以利誘民,使無鬥誌,亦可明告百姓,凡搶劫洋貨,任其自分,官不過問。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醇親王奕譞
這就是堂堂一國重臣公開發表的流氓言論,有意味的是,這種流氓言論當時引發一片叫好,並被落實行動。
1870年夏天,因為盛傳洋人教堂殘殺嬰兒,挖眼剖心,憤怒的數百圍觀百姓打死了法國領事豐大業及其隨從,又衝入法國教堂,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二十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雇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憤怒的天津民眾將焚燒教堂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鬧大,派人將教堂前的浮橋拆毀以阻人前進,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稱的提督陳國瑞卻派人重搭浮橋,並立馬橋頭為群眾助威。
官匪一體,竟如蠻荒之境。
天津教案發生後,頑固派認為民眾為保衛官員而殺洋人,說明“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機會,把京城的“
夷館”盡毀,將京城的“夷酋”盡戮。頑固派代表、內閣學士宋晉奏稱育嬰堂“有罈裝幼孩眼睛”,連慈禧太後也深信此點,向曾國藩下諭道:“百姓毀堂,得人眼人心。”
在頑固派的影響下,朝廷態度越來越強硬,對派往處理的欽差曾國藩下令說,“此後如洋人仍有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並表示要在各地作軍事準備。
曾國藩到天津後,經過一番認真勘察,確認迷拐、挖眼剖心等均係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醃製的洋蔥。
曾國藩本想大事化小,息事寧人,把“犯官”從輕發落,不曾想,西方列強高壓下,朝廷又命曾國藩不得包庇,曾國藩不得不又加碼處理,這一來一往,曾國藩成了左右不討好的曆史罪人。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
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協助曾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權要紛紛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教、懲處媚外官員。困局由洋務派官員解開,但頑固派卻得到一種“
道義上的力量”,使洋務派在輿論上反成為國家、王朝的罪人。
替罪羊、曾協助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悲歎:“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艱難,自然容易附和不著邊際的高論,一旦事情失控,與列強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隻會空談的人不僅不承擔禍責,“反得力持清議之名”。
出爾反爾,看菜下飯,看打回話,成為清廷末期專有的範式。隻是,挨打歸挨打,割地歸割地,殺臣歸殺臣,清廷卻始終改不掉拿起棍立正,放下棍囂張的德行。
清廷,真乃一個怎麽都揍不醒的奇葩國。
D:我先任性,子孫還債
縱觀清末曆史,清廷就是一個拽著不走打著倒退的欠揍貨。正像作者所說,本來可以溫和實現的政改,在清廷和頑固派的一再抵觸拖延下,後來終於病入膏肓,連統治階級內部都滋生反對派,以至於革命火起,迅速燎原,這其中響應者,非隻革命黨,更有積怨已久的各路諸侯和原本順從的良民。
盡管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但在1898年的時候,清廷尚有推動變革的主動權,但清廷一拖再延,最後完全成為變革的敵人,革命的目標,其統治的合法性在國人心目中盡失。
晚清,1998年和1906年,清政府曾兩次嚐試“改革”,被宣揚得如火中天的“戊戌變法”,其實隻是康有為等人拉一個弱弱的光緒帝大旗,進行羞羞答答的行政調整而已,即便如此,仍然遭到頑固派群起而攻,譚嗣同等六君子更是掉了腦袋。而1906年這次由原來的頑固派首領慈禧親自發動的“新政”,最後竟然演變為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改革騙局。
本來,在1898年戊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但它卻拒絕改革,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隻是在經曆了兩年後的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之後,它才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地開始“新政”。1901年
1 月 29
日,慈禧在西逃途中即以光緒的名義頒下諭旨,表示願意“變法”,當然仍強調“不易者三綱五常”。不過為時已晚,形勢已經劇變,尤其是經曆了庚子流血的巨變,它的統治合法性開始遭到普遍的懷疑。由一個合法性遭到嚴重質疑的政府來領導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進行調整和再分配的改革,已經理不直氣不壯。更重要的是,時過境遷,幾年之後再做這些已遠遠不夠,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協。但清政府對此似乎並無察覺,各項亟須的、能緩和各種尖銳矛盾的“
新政”主要內容一拖再拖,遲遲不肯出台。
遲至1908 年,清廷著名的《憲法大綱》出台,共二十三條,頑固維護皇權,毫無改革誠意,於是舉國嘩然。
對此,激進的革命派和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認為其“偏重於命令權”,“專製之餘風未泯”,“最足假以文飾其專製”,並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陰險之手段,假欽定憲法之名,頒空文數十條以愚吾民”,必“動搖國本而傷君民之感情”。在實際預備立憲過程中,清廷總以條件不具備一再拖延,溫和的立憲派終於也認識到“
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 1911年5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十三人組成,其中九名為滿人,漢人隻有四名,而在這九名滿人中竟有七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
隻是一個幌子、
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麵目。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墓,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社會亟需快步走的時候,當政者卻在倒行逆施。
《曆史的進退:晚近舊事與集體記憶》作者說,正是清政府的冥頑不化,政治上拒絕改革,經濟上搖擺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從來溫和謹慎的士紳商董都開始遠離它、拋棄它進而反對它!昔日所謂“縉紳之家”比今日所謂“中產階級”還要“多產”,因此更加接近、貼近、親近統治者,更加禱盼和平穩定,更加溫良恭儉讓,他們尚且態度大變,又怎能指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是“激進”呢?武昌起義時孫中山遠在美國科羅拉多,事先並無預聞,第二天才從美國報紙上得知此事,亦從一側麵說明清王朝的轟然坍塌實因其統治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換句話說,是清政府的顢頇與極端頑固,最後“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進”。
雷頤說,縱觀晚清曆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製一定局麵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革;隻到時機已逝、完全喪失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但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願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始終是被形勢推著走。這樣,它後來便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直到完全破產。
1907年初,仍置身保皇黨團隊的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了《
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不得不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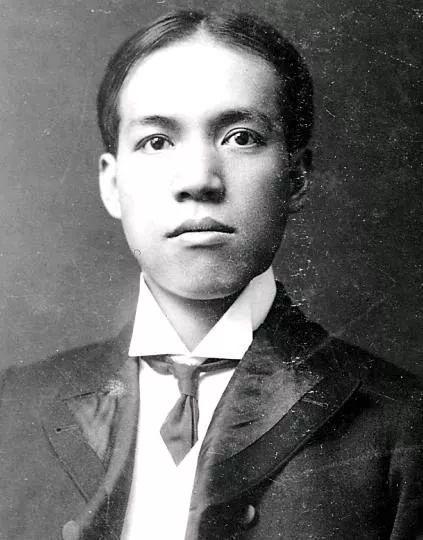
華客網:大陸熱文:末世癲狂自淫 世界早晚是我大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