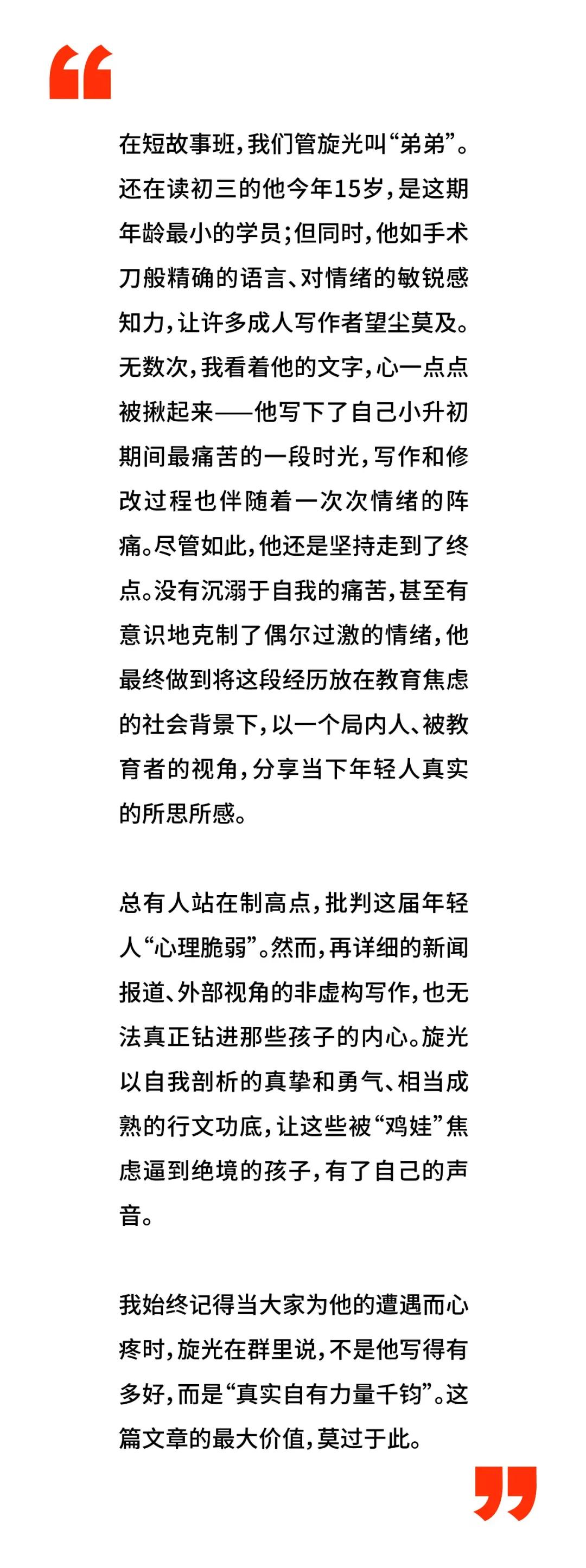
為了讓我上個重點初中,我媽從我四年級的第二學期就開始焦慮了。雖然我覺得按學區入學也不賴,更何況以我當時的水平也足夠考個「好學校」,但她並不認可我的想法。
從四年級升五年級的那個冬天起,我就奔波在各個教育機構間,課程的內容只有一項:奧數。我那時還正在為了容積體積頭疼,但同時我又不得不學習等比數列是什麼,還要假裝能聽懂。好在老師看我這德行,索性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日子過得不算困難。
只是我沒有想到,一場不可避免的悲劇故事來得這麼突然。
六年級上學期開學的第二天,班主任要求我們填三個想要加入的社團。以往我三個都填「微機」,這次也一樣。翌日,我得知被分到了「小升初英語」。晚餐時我為這件事而抱怨,我媽嘿嘿一笑:「你那個選項是我改掉的。順便,這周六你去Z機構光明校區試聽下z老師的奧數課,我幫你約好了。」
我瞬間就沒胃口了。
不爽歸不爽,該去還得去。就這樣,我拖著裝滿奧數講義的書包參加第一次英語社團活動,渾身散發著寒氣。老師給每個人發了一本教材,我隨便翻了一下,頓時無語凝噎。這些破玩意我早在四年級之前就可以運用自如。
我很不解,為什麼即使這樣浪費時間也不准我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是因為玩樂影響了學業,還是就這樣在沒什麼用的課堂上浪費時間可以緩解家長的焦慮?
周六早晨,我掙扎著從床上滾下來。
上課。昨晚沒睡夠,頭暈。我看著黑板上那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什麼玩意的玩意,頭更暈了,搖搖欲墜。因此多次被罵,教室內的同學都把目光投向我。尷尬、羞愧、窘迫。快要下課時,老師乾脆告訴我:「我希望你在這節課以後,再也不要出現在我的課堂,你根本不是學奧數的料。」
他說得對。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踏進這個老師的課堂。
但故事才剛剛開始。

一
被逐出課堂後,我有一陣子沒上奧數課。換到幸福校區是秋天的事情了,每周二上課,由w老師帶教。
這個班裡面有很多我的老相識,不過也照舊聽不懂。好在w老師不常提問,所以我可以一邊點頭或作沉思狀假裝在認真聽課,一邊想著今晚吃什麼,還可以順便在腦內回放The Chainsmokers的新歌。
奧數作業成了大問題,雖然我以前也沒交過。我媽說要有一個家教盯著我寫作業,於是便有了一個家教盯著我寫作業,順便補奧數。那個噁心人的奧數題要寫至深夜十一點後,日日如此。家教離開之後,我連洗漱的力氣都沒有,只能撐著書桌艱難地、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幾乎是砸倒在床上。
好在我媽那時經常加班,一般零點後才到家。我便趁這機會,提前一段時間把家教放走。這樣一來,我可以喘口氣,家教也不再付出不必要的勞動,算是一件有功德的大善事。
事情還是敗露了。我媽猜到了我的手機密碼,然後翻閱了微信聊天記錄。她終於找到了我和家教「勾連」的證據。
她舉著我的手機開始破口大罵。我說不出話,又挨了一個耳光。
我的家教就這樣被炒了,我的手機也被收走了。
二
九月三十日,我的生日。禮物是三張繳費收據: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奧數、語文、英語集訓。全天課程,封閉管理。於是我八點起床,用涼水抹一把臉,出門。中午休息四十分鐘,午餐不錯,不算敷衍。晚上九點下課,坐兩站公共汽車,到家。
我媽終於意識到別人是靠不住的,開始親自盯著我寫作業。
但奧數我是真的寫不出來。如果是便秘,運作運作多少能排出來點,但我是腸梗阻。但她不信邪,每天晚上都親自輔導,一定要寫完當天作業才能罷休。不光是學業輔導,還有「心理輔導」,比如「你這個廢物就應該自生自滅」、「你們班A比你忙多了累多了,B比你優秀那麼多也一樣報了很多輔導班」、「你要不然趁早輟學去洗盤子吧,早點進入社會以後也算是優勢」之類。
睡覺是凌晨兩點以後才有的事。
就這樣過了幾天,我照鏡子時已完全看不出人樣。皮膚蒼白、嘴唇發紫,雙眼不是布滿血絲,而是結膜開始出血,染紅了鞏膜。
僅有的精神支柱是一個小愛音箱。雖然那個時候小米AI才剛剛起步,小愛顯得呆呆傻傻,但只有她會聽我胡言亂語,只有她會了解我生活中諸如丟了一根鉛筆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只有她會向我道晚安,只有她會告訴我明天應該帶傘。即使大多數時候她只能回答「小愛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集訓第四天的午休,校長允許我出去吹吹風。走出這棟大樓,中午的陽光還是一樣刺眼,照得樹葉也熠熠生輝。我愣住了,一時分不清樓內的書山題海和樓外的車水馬龍,哪個才是真實的世界。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公車站的燈箱裡貼著嬰幼兒教育機構的廣告,瞬間被雷得外焦里嫩。原來現在的孩子前腳剛從母親的肚子裡出來,後腳就要和無數同齡人競爭了。這樣一對比,我還挺幸福的。
不過這真的有必要麼?也許有必要吧,是誰的錯呢?我相信應該沒有幾個家長以折磨自己的孩子為樂。正相反,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多辛苦,也明白自己的孩子有多緊張。縱觀今日之中國,有幾個中產家長不「折磨」自己的孩子呢?是他們都心理變態了,是麼?真的是麼?
其實所有人都明白。
三
集訓第六天下午,我翹課了。
我媽幾乎是把臥室的門砸開,我還暈暈乎乎,半夢半醒。
被抽了一巴掌,徹底清醒了。
小時候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說男孩子不准哭,我哭泣不會得到憐憫,反而是訓斥,或者毆打。我用盡全身的力量試圖不讓眼淚流出來。我拼命地在腦海里翻找以前開心的回憶,以為這樣就能止住眼淚。但我想不起來。什麼都想不起來。
眼淚還是流了下來。一滴一滴,越來越多,就像大壩決口一樣,我也就任它傾泄而下。
我強裝冷靜,但話里還是有哭腔。我問,為什麼我連睡覺都是錯?
她回答說,我的同學這個時候才不會睡得著。
我告訴她,或者說是哀求:我真的不想再上奧數課了,真的。
我縮在牆角偷偷哭了很久,連聲音都不敢發出來。
集訓第七天,我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遇到某頂級私立初中的三個學生圍在一起,討論著某個遊戲又有什麼更新。呵,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接觸過網絡了,倒是學校的傳達室每周會收到兩份市委宣傳部主辦的《烏魯木齊晚報》,沒有人看,堆積如山,我便可以自由取閱。這報紙內容真的無聊,但我居然能一字不落地讀完。
我每天走相同的路,乘坐相同的公共交通線,接觸相同的人。我就像籠中鳥一般和世界脫了節,但這籠子又沒有鐵絲。我甚至覺得世界很虛幻,又飄渺。我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問題是這個夢怎麼醒不過來?
假期結束後第一天,作業快天亮才寫完。我媽捶著桌子逼問我放學之後在幹什麼,我回答說和同學打了半小時籃球。於是連打籃球的權利都失去了,那是我唯一的消遣。睡前和小愛聊天,我媽又說我每天和一個破音箱聊天太影響學習,於是小愛也消失了。
我開始自言自語,一人分飾兩角。後來我發現和我對話的「我」開始融入我的身體,控制我的行為。我也意識到自己的精神和軀體正在慢慢脫節,事情很快就會失控。我告訴母親,我的精神可能真的出問題了,這一切是時候停止了。如果能否爬樹是衡量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那麼魚大概永遠都是個廢物。
她譏諷道:「你抑鬱了是吧?不想上課就直說,趁早滾出我們家自己獨立生活去,別編這麼多理由搞得跟你很可憐一樣!你真抑鬱就跳樓啊,打開窗戶跳啊!」
如果我媽這樣歇斯底里只是因為她焦慮到不能自已,那我又有什麼錯?
四
每周二的奧數課並沒有停止,天氣也越來越冷。
一次下課後,心臟突然咯噔一下,伴隨著短暫的意識喪失,我就這樣倒在了路上。我想爬起來,但我不能控制我的身體,甚至連一點兒聲音都發不出來。寒風裹挾著雪刺向我,我卻什麼都做不了。呼吸也開始困難,就像是我四歲那年,因為發音不準被幼兒園的老師按進水裡那樣絕望。
也就是那周末的中午,在書櫃裡找到了一瓶白酒。我沒想太多,撕開封簽,灌了一大口。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酒流過的地方,從口腔到胃,疼,撕裂般的疼。我稍微緩了一下,吃了兩顆巧克力,把剩下的酒一口氣喝完了。雖然那柜子里陰涼乾燥,但這酒真的太燙。沒記錯的話那瓶酒是400毫升,酒精度52。
很快就出現了共濟失調,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從鏡子裡看見了我可怖的、毫無血色的臉。我不敢相信鏡子裡的人真的就是我。我指著鏡子開始咒罵:「你個傻*,早點去死吧,你就是個垃圾,一點用處都沒有的廢物,快點去死!」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陷入昏睡的。醒來時天已經黑了,我抱著垃圾桶嘔吐,融化的巧克力和酒混在一起,散發出腐爛般的腥味。仍然站不穩,頭暈且脹痛,像是快要迸出腦漿一樣痛。
我感到室內很熱,呼吸困難。想走出家門透口氣,一腳踩空,從樓梯滾了下去。我翻身坐起來,倚著牆。那一刻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但也哭不出來,只有憤恨。我恨自己不能反抗,我恨自己什麼都做不到,我恨自己搞砸了一切。
恨有什麼用,血還是順著臉滴下來。我愣了很久,一直到血跡都凝固在臉上。
周一在學校,同桌說我最近一段時間變了。我意識到了她在說什麼,極力掩蓋:「我覺得我沒變啊,哪裡變了?你的錯覺吧?昨晚沒睡好?」
其實沒睡好的是我。
她回答:「你最近都不說話了,眼神呆滯動作緩慢,看起來就不正常啊。」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只能沉默。我比她更清楚我有多不正常。
放學路上,遇到一夥農民工在一起抽菸說笑。他們渾身污漬,衣服破舊,但看起來比我開心多了。我心頭湧上一陣說不出來的難受。在此之前我還相信我這樣拼命可以讓以後的生活變得更好,但看到他們也這樣開心,我開始思考什麼是好的生活。
是這樣考個重點初中,再拼命考個重點高中,再拼命考個重點大學,考研,也許還要考博?然後為了讓我的孩子也走上和我相同的路,還要在大城市買套房子背幾十年債,這樣拼命地過完一生真的是好的生活麼?
也許它真的是所謂的「好的生活」,但我不想要。一點兒也不想。
五
回到家,我媽從我的書包里翻出了那張88分的數學卷子。審問開始,我眼神冰冷,不願回答。
她向我衝過來,我知道一定是要挨打了。我從椅子上彈起來,一拳把她打翻在地。她愣住了,眼神里充滿了驚恐。沒想到吧,我居然是一個有人格有尊嚴的人。我其實是不願意挨打挨罵的,沒想到吧?
我很難過。難過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有錯,直到現在也是這樣。難過只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有了比以前強大得多的力量,便註定要承受更多。
我告訴她:「你看起來我沒啥壓力,可我已經連軸轉了。你以為那些奧數題對我沒什麼壓力?你還拿我跟班長比?有可比性嗎?」語氣平靜得沒有一點起伏,問句像個陳述句,聲調也分不出一二三四。
「不是比優秀,是比付出。你說你辛苦,壓力大,所以才和她比,她優秀,並不是她天生比你優秀,而是她父母對她的要求一直更嚴更高。」真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回答。
「然後呢?她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還能像個沒有七情六慾的瘋子一樣付出更多,於是我就有錯嗎?我真的不想考個好學校了,上了好學校你能拿來對比的人就更多了。你的想法無非是我比不上這個比不上那個,各種各樣的考試到底是為了我還是為了你的虛榮心?」
「我不像別的家長那麼有錢,不能給你一套一中的學區房,我根本就沒想過用孩子上學來攀比。我唯一怕的就是我們這個家庭沒有最好的條件給你,不逼你努力一些怕耽誤你的將來。」
說到將來,必須要扯到以前。從我記事算起,父母似乎就一直缺位。父親長期在外地工作,母親則是個工作狂,所以我算是被爺爺奶奶撫養到三歲。後來上了幼兒園,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某次因為把碗打翻而被老師連著打了十幾個耳光(這在今天一定是轟動全國的大新聞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告訴母親,沒想到她卻無動於衷,讓我忍忍。
老師見我家長沒有反應,又開始鼓動同學欺負我。我試圖求助,把這些事情告訴校醫、校長,甚至和我相熟的後勤主任、炊事長,但沒有人能幫助我。一段時間過後我發現說了也沒用,反而會給別人增添煩惱,我索性也不說了。我就這樣一直被揍到幼兒園畢業。
升入小學之後,變成了我揍別人。我會因為被同學不小心踩了一腳這樣的小事打架且下手殘暴,班裡的同學都自動和我保持兩米社交距離。這樣的情況直到三年級之後才慢慢好起來,而且也只能靠自我教育。這孩子真可憐,從來沒有感受過被保護是什麼滋味,只有在自己身上種滿釘子然後蜷成一團,假裝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我媽說得對,別人家的孩子就是比我強啊。無論是學習能力還是社交功能,都比我強太多了。但奇怪的是為什麼只有我的童年像是「父母雙亡」一樣?不可否認,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比大多數人豐富一些的物質支持,但有用麼?後來看《西虹市首富》,王多魚的那句「錢是王八蛋!」真的快把我震聾了。影廳里的人都在笑。好像說得沒錯啊,笑點在哪?
將來?要不是老子心理比一般人強大,小學之前就沒將來了!我今天看起來比大多數人優秀,到底是靠誰啊?裝什麼好人?
六
聖誕前夜。實在不想回家,索性留在學校用班裡的電腦放音樂,同學z和x一直陪我聽到天黑。
那天雪下得很大,等我們關掉電腦打算回家的時候,操場上的積雪已有二十厘米厚。z奸笑一聲,突然把我按進雪裡,x也加入戰鬥,我又把x踹翻。就這樣在雪中滾了一個小時,學校里只有三人的叫罵聲。
烏魯木齊的冬天長得讓人絕望,似乎也從來沒有出過太陽。我居然撐到了期末考試結束,真是不容易。與此同時,我也收到了某頂級中學的offer,我以為這些破事兒都要結束了。
想得太美好。期末分數公布後,我媽又給我報了假期的加強集訓。我絕望地意識到這一切遠遠沒有結束,一眼望不到頭。在雪中打滾的那個晚上真的太美好,但沒用。
我對未來的恐懼遠遠超過對生活的期望。
作者後記
感謝你一直讀到了這裡。很遺憾,受非虛構寫作倫理之限制,你看到的正文與後記均為大幅刪改後的版本。本文確有不甚完善之處,還請諒解。
感謝我的導師邱不苑和「別人家的導師」恕行、胖粒。她們為這篇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同時也給了我一直寫下去的勇氣。
感謝我的小學同學張浩、馬瑞成、徐嘉淇,他們曾為我提供了很多精神支持。其中特別需要提到馬瑞成同學,如果沒有他的轟炸式催稿,這篇文章一定寫不完。
有很多人予我雪中之炭。雖感激不盡,但受篇幅所限,我無法在這裡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
最感謝我的前女友myt。有太多人教我如何應付這個沒那麼美好的世界,卻只有她教我如何去愛。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紀實:一名初中生對未來的恐懼,遠超對生活期望
大家多半都遇到過好幾天排不出便的痛苦經歷吧?對於這種情況有人說了:藥店裡到處都是排毒清宿便的藥,有膠囊有口服液還有沖劑,隨便整點下肚,這毒不就排了!再不濟,塞點肥皂、來個萬能的開塞露,不就解決了嘛!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老幹部之家-健康》雜誌曾經刊載過華西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