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陸續發生18起自殺事件(據長期關注的學者統計),造成14死4傷的悲劇,被輿論稱為“連環跳”,引發社會對“血汗工廠”的大討論。4名不幸又幸運的傷者中,湖北女孩田玉當時還不滿17歲,從此隻能坐在輪椅上生活。十年裏,她奮發過,消沉過,終於找到一份普通而充實的工作和一個愛的人,得以離開對外界關注的依賴,重建自己的生活。在田玉身後,更年輕的工人走進工廠……

2010年,富士康主板生產線上的女工。 (王軼庶/圖)
已經沒有人——包括田玉自己——能說清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她不願回憶過往,但她清晰地知道,當初作出的那個決定,她後悔了。
當年還是南方周末實習生的劉誌毅,在富士康臥底時,時常聽人談論自動化替代人力的問題,當時的說法是“替代成本會很高,時間也會很久”。
本文首發於2020年1月2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十年·未忘”之“新聞續集”
26歲女孩田玉滿意如今的淘寶客服工作。一周分早班、中班、晚班,雖然上班時間不同,但她始終可以待在家裏。一個月上二十餘天班,總能休息四五天。工資足夠養活自己,還可以和丈夫朝夕相伴。
她在2018年國慶節期間認識現在的丈夫,不久後的元旦就結為連理。上晚班時,00:30才下班,丈夫會等著她下班才一起入睡。
能記起田玉另一個身份的人已不多——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中的幸存者。當年3月17日清晨,才到富士康上班一個月的田玉沒去做工,從4樓宿舍一躍而下。很難說她幸還不幸,她成為富士康18名自殺者中的4名幸存者之一。前一天,她經曆了找不到工資卡、被各級領導扯皮推諉、身無分文走回宿舍等等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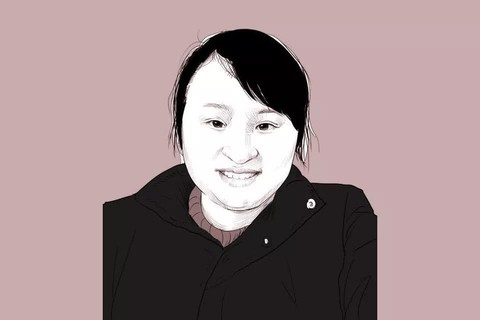
田玉 (農健/圖)
已經沒有人——包括她自己——能說清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她不願回憶過往,但她清晰地知道,當初作出的那個決定,她後悔了。
2010年讓整個中國製造業難忘。一名富士康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0年時,富士康全國的工人急劇增至一百萬左右,基層管理並未適應工人劇增的工廠規模,很多問題明顯地爆發。富士康是經濟全球化進程裏,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薄利多銷的代工企業背後是難以消弭的勞資矛盾。
2019年底,南方周末記者重訪深圳龍華富士康。如今的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僅十幾萬人,而10年前,這裏生活著三十多萬謀生者。這名富士康內部人士說,2010年慘劇發生後,富士康意識到規模過大帶來的管理難題,也有意識地在減少工人數。同時,富士康的全國布局在變遷,成都、鄭州等西部地區的園區逐漸成立,一些工人可以在離家更近的地方打工。而另一重背景是,中國代工業的內外部競爭在日益加強。
1 “好好生活,再生個自己的寶寶”
活下來的田玉,在深圳經曆手術,幸運地蘇醒、恢複。好幾個大學生陪伴在她身側,捱過一段黯然的時光。她感念曾幫助她的那些大學生,如今,她對遇到的大學生也抱持特別的好感。富士康承擔了她在深圳期間治療的費用,再給她18萬元作為賠償。在深圳治療7個月後,田玉回到湖北襄陽的家。
她持續在武漢、襄陽的康複中心接受治療,逐漸恢複了部分自理能力,可以自己穿衣服,上廁所,還有洗澡。恢複雖緩,但總有進步。武漢的治療費有2萬多元,而襄陽那家鄂西北工傷康複中心則免費為她治療。
在襄陽治療的時候,她認識了一位心理谘詢師。無論大事小事,她都會去找那位谘詢師傾訴,在田玉的敘述裏,那位和她父親差不多年齡的谘詢師,就如同她的知己,也和她一樣喜歡種植物。
2010年,一些來看她的人送來一本手工藝書籍。她對此頗感興趣,開始根據書裏的內容做些手工藝品。到了年底,她製作了一批布製拖鞋。次年,布鞋在微博經一些明星轉發,悉數賣出。2012年,她開始做洋娃娃,每做1個洋娃娃,需要1周時間,她做了四五個。但最終洋娃娃質量不過關,沒能如願賣出。
接下來的2013年,她的生活陷入消沉。腿上的傷口複發感染,經常發燒,在家躺了大半年。田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兩年,她沒工作,也沒目標,不知道活著的意義。她時常發呆。發呆時就會看著家裏的植物,玉樹、千足葵、幸福樹,盯著植物的時候,“心情也變得美麗”。那時她臉上很少掛笑容,而她本來是個愛笑的女孩。
2014年,有位紀錄片導演來看她。導演和她長談,聊人生價值,亦勸她振作,更具體的內容,田玉也想不起來了。後來,導演給她寄了34本書,所以那年剩下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讀書。她最喜歡李娟寫的《阿勒泰的角落》,因為書裏寫的是一些她永遠無法抵達的生活——生病後她再沒有機會旅遊,阿勒泰的草原和湖水讓她心馳神往。還有書裏生機勃勃的人,女孩在清澈的溪流裏洗頭、洗衣,在草原上牧羊。
李娟一家跟隨季節流轉遷徙於夏牧場和冬牧場之間,流動的生活讓她走遍阿勒泰的各個角落,而田玉被固定在一張窄小的輪椅上了。
心情逐漸平靜,2015年,她找到一份淘寶客服工作,生活開始變得充實。工資受到答問比、響應時間、成交率的影響,她每天在電腦前坐8小時,雙十一、雙十二還得加班。
生活日益向好,內心總有小小遺憾。當年去深圳,她不到17歲,在技校財會專業畢業不久,對大城市有向往。如今在襄陽農村,一切都那麽平常、無聊。農村裏打的難,無障礙設施配備不完善,輪椅上的她出行並不方便。
但她心裏明白,可預見的未來裏,她會一直在這待下去。“我現在的願望就是和我老公一起好好生活,再生個自己的寶寶。”她說。
2 田玉的後來者們
田玉是富士康百萬工人裏普普通通的一個,不幸卻又幸運的那個。
一名曾於2007-2009年在富士康從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富士康對流水線的管理極其精細,小到工人完成每個步驟的時間,每天在車間要走的路,一個零件到另一個零件的距離。而內部等級眾多,從員到師再到管理級,上下級分明。10年過去,富士康仍像廠房內部的一台台機器一樣,精密地運轉,效益最大化,這是整個製造業普遍的追求。富士康用軍事化的管理,讓工人像一個個零部件那樣被嵌入流水線。
煙台富士康員工普克是新一代打工者。他工作了六年,仍然沒有從基本的員級提升到更高的師級。在富士康,他鮮有朋友,但相比孤獨,他更容易感到迷茫:“一個月拿三千塊,天天上班,也犯愁,看不到出路。”普克說,不工作時,他一般會刷手機和睡覺,看抖音、快手和西瓜影音上的搞笑視頻,有時也會瀏覽知乎問答。他的知乎首頁上有很多關於煙台富士康工廠的回答,與交談中透露的迷茫不同,在回答中他曾提到:“為一個普通人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富士康最大的價值。”
“當初犯下的錯,誰讓自己不好好上學。”他這樣解釋自己如今的處境。
和普克不同,淮安的於木畢業於二本院校,一開始就是師級員工。他被安排在周邊部門,工作相對清閑。剛畢業到淮安富士康時,他很不適應,常常感到和其他員工有隔閡,員工打飯時不排隊的習慣也讓他無所適從。高峰期下班的出口處密密麻麻都是人,彼此推搡擠挨。二本畢業的他不甘於永遠在富士康幹下去,他將這段工作經曆看成自己的跳板,“也不知道自己會幹到什麽時候,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暫時對付著幹”。
社科專家的研究裏,不同時代的打工者,麵臨著不同的時代境遇。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第一批打工者進入城市,通過打工賺錢後,都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蓋房子,娶媳婦。1980年代後出生的打工者與父輩不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戶口門檻讓他們很難真正成為“市民”,但農村的土地又越來越難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他們常會陷入留不下來又回不去的困境。
而1990年代後出生的新一代打工者又有差異。即便考不上大學,父母也會期望他們有更好的教育,因而很多年輕人都進入職業學校,他們自己也會期待職校教育能給他們帶來技術上的提升,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但現實往往很難實現父母和他們自身的期待。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11-2015年,深圳富士康基本工資漲幅為11.4%到12.8%,而同期的物價增幅為16.9%。更嚴重的是,富士康工人的工資通常由基本工資、加班工資與福利補貼等部分構成,基本工資增加的同時,由於加班減少,補貼取消,很多工人實際到手的工資更少。和10年前一樣,工人仍要依靠加班獲取大部分收入。於木說,淮安富士康生產工人的工資已經四年多沒漲,2014年時每月三千多元,2019年仍然如此。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係教授潘毅觀察到,城中村改造是另一個關乎務工者生存境況的背景,這項本來出於好意的政策,也增加了工人的生活成本。改造之前,他們的房租可能隻要四五百塊,但改造之後普遍要到八百到一千。
3 十年過去,工人並未被機器取代
但10年間,工人的富士康生活依然改變了很多。
2019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記者走入富士康龍華科技園,這也是富士康總部所在。
這是個如同高校的工業園區,超市、餐廳、咖啡廳、觀影室,一應俱全,工人上班無聊、機械、重複,下班喜歡玩網遊,工業園裏就相應配套了網咖。還有中醫診所,針灸、推拿,服務著十餘萬工人,他們會有肩頸方麵的職業病。
2010年悲劇發生後,富士康在員工宿舍的陽台上都裝了鐵絲網,以期擋住某種衝動。幾年後,隨著自殺案例減少,這些網也都逐漸拆除。田玉跳樓一個月後,2010年4月21日,富士康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至今還在發揮作用。關愛中心裏,有傾聽室、納言閣、宣泄室等用以處理員工心理問題的區域。宣泄室裏的假人和拳擊手套特別搶眼,心理壓力大的工人可以到這裏,“全副武裝”宣泄,時間一般在30分鍾內。
關愛中心還設有兩個熱線:心靈熱線,由專業的心理谘詢師接聽,提供心理谘詢;而關愛熱線,則是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比如工人找不到鑰匙了,也可以找關愛熱線解決。
工會也提供免費技能培訓。在深圳總部工作的李九一也是二本畢業的。平時喜歡電腦的他,報名參加了C語言課程,如今他已經轉行,做起了程序員,工資也提高了。他說在富士康接受的免費課程使他受益很多,他感激富士康給自己帶來的成長。
普克也聽說過工會舉辦的線下活動,如跳繩、拔河、知識競賽等,但在他看來,基層員工在長時間的繁重勞動後,很難抽出時間來參與這些活動,“定人定崗,你走了,工作怎麽辦,產量怎麽辦?”這些娛樂活動也大都由比較清閑的崗位上的員工參與。富士康另一名官方人士有不同說法,一開始,富士康常以園區為單位舉辦活動,後來發現各個部門、產線忙碌周期不一,根據具體訂單有所不同,舉辦活動又以各部門主辦為多。
至於工會的實際作用,多名富士康工人表示,“小問題能解決,大問題也解決不了”。在於木眼中,工會隻是一個節假日發發禮品、偶爾組織活動的部門,工人很少參與勞資談判過程。
人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動化。
當年還是南方周末實習生的劉誌毅,曾在富士康臥底28天。他記得,在他臥底時,富士康時常有人談論自動化替代人力的問題,當時的說法是“替代成本會很高,時間也會很久”。
但替代其實不久後就發生了。李九一2011年在富士康實習,一開始在流水線上給遊戲機兩邊塗膠水。一段時間後,他被調劑到包裝崗位,因為原來的工種被機器取代了,機器可以重複進行塗膠水的工作。
前述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工程師也說,富士康的機器人
研究早在連環跳發生的2010年前就已開始,研發投入並不小,有專門研發部門,其他部門也有對接人員。
前述富士康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到2016年,全國富士康工廠大概有6萬台機器人,但取代的工人數量不好統計,有些工人會被替換到其他產線,有些產線會讓機器人和人工配合。而且富士康內部不太傾向“機器換人”這種提法,更喜歡說“解放工人生產力”,企業也不願公布相關數據。
不過,他也強調,機器人在每個行業運用的形態和程度都不一樣,在電子行業就不像汽車製造應用那麽深入,對自動化的水準要求也更高。如今機器人技術還隻能做一些重複、繁雜、機械性較高的工作,例如搬運、拋光打磨,涉及後端製造更精細的工作,還得依靠人來完成。“人可以做得更好”。
工人也沒有感覺到因為自動化裁人。“裁人是很少的。一到春節就會走很多人,工廠人員如流水,廠裏對工人的需求還是很大。”富士康龍華科技園裏一名工人說。
華客網:富士康連環跳幸存者田玉:十年來,親手重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