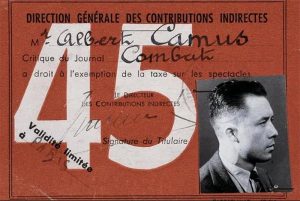
譯者按:2016年3月,是加繆一生中唯一一次美國行的70周年。紐約市舉辦了一些紀念活動,其中包括在當年他曾演講的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演員Viggo
Mortensen重新朗讀當時的講稿《人類的危機》。本文根據英文朗讀稿聽譯,並結合法文版本譯出,參考了馮壽農、黃旭穎譯文。
女士們、先生們:
當我被邀請前往美國進行一係列演講時,我有些疑慮和猶豫。我還沒有到足以演講的年紀。我更善於思考,而不是發表總結性的言論。因為我沒有任何關於所謂「真理」的結論。不過有人很禮貌地告訴我,我的個人觀點並不重要,關鍵是介紹一下法國的情況,讓聽眾形成自己的觀點。有人建議我談論法國當代戲劇、文學、甚至哲學。我回答,那不如談談法國鐵路工人的成就,或北部礦工的工作得了。但他們有理有據地反駁說,人應量才而為,不同專業領域的問題要交給該領域的專家。顯然我對鐵路道岔一竅不通,但卻從事過不短時間的文學創作,自然應該談論文學而不是鐵路了。
最後,我明白了。我應該談論我熟悉的事情,並介紹法國的概況。確切地說,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決定既不談文學、也不談戲劇。因為文學、戲劇、哲學、科研,以及整個國家的努力,反應了人類的本質問題、人性和生活的掙紮——如今,我們正受困於此。法國人認為人類依然受到威脅,他們認為,為了活下去,必須對某種觀念進行拯救,以從攫取著這個世界的危機中逃離出來。基於我對國家的忠誠,我決定談論這場人類的危機,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這一代人的道德體驗盡可能清楚地描繪出來。因為我們見證了這場全球危機的誕生,我們的體驗多少能幫助大家了解人類的命運,和當代法國人的情感的某些方麵。
一
首先我想對這一代人做出定義。在法國和歐洲,那些和我年紀相仿的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或此期間出生的,青春期遇上全球性經濟危機,到了二十來歲,希特勒就上台了。西班牙戰爭、慕尼黑協議、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1940年的法國淪陷、四年的被占領和地下抵抗運動成為他們成長教育中的補充教材。因此,我們可以被視為是有趣的一代。為了便於表述,此刻我想不以我的名義,而是以一群三十來歲的法國人的名義和你們說話。他們的智識、心靈成形於那些可怕的年頭。他們和他們的國家一樣,以羞恥為營養,以反抗為生。
是的,這是有趣的一代人。他們麵對著一個由父輩所創造的荒誕的世界;他們什麽也不相信,在反抗中度過。他們時代的文學完全反對清晰,反對敘事,甚至反對語句。繪畫是抽象的,以反抗寫實主義、現實主義和和諧。音樂拒絕旋律。至於哲學,他們告訴人們真理並不存在,隻有「現象」。史密斯先生,杜蘭先生,沃格爾先生都是存在著的「現象」,但這三個「現象」之間毫無共同點。我們這代人對道德的態度則更加分明:民族主義似乎是過時的真理,宗教是一種逃避,二十五年的國際政治使我們懷疑一切純潔性,並得出如此結論:大家都沒有錯,因為大家也許都是對的。至於我們社會的傳統道德,似乎始終被我們認為是怪物般的偽善的存在。
所以,我們活在否定之中。當然,這不是什麽新鮮事。其它時代、其它國家,在曆史的其它時期也有過這樣的經曆。但這次的區別在於,對於一切價值感到陌生的這批人,不得不調適個人立場,去適應恐怖、殺戮的現實情景。局勢使他們相信,人類也許正經曆危機,因為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最揪心的矛盾中。他們前往的戰場有如地獄——如果地獄果真是對一切的否定。他們既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暴力,但他們不得不接受戰爭、施行暴力。他們唯一憎恨的是憎恨本身,然而他們被迫學習憎恨這門艱辛的科學。他們不得不麵對恐怖,又或者,是恐怖找上了他們。他們所麵對的局麵,我想通過四個簡短的故事、而不是籠統的字眼來進行描述。盡管世界已經開始遺忘,但它依然在我們心中燃燒。
1)在歐洲某個首府城市一所被蓋世太保占領的公寓裏,兩名還在流血的囚犯在經曆了一整晚審訊後,發現自己被捆綁起來。大樓的管理員開始認真做家務,也許是剛用完早餐,她心情很不錯。當其中一個被施虐的男人指責她時,她憤慨地回答:「我從來不管房客的事。」
2)在裏昂,我們的一位同誌從牢房裏被拉出來接受第三輪法庭審訊。在上次審訊中,他的耳朵被狠狠地撕裂了,頭上紮著繃帶。審問他的德國軍官和上一輪是同一個人,然而他用一種同情和關懷的口吻問他,「您的耳朵怎麽樣了?」
3)在希臘的一次地下抵抗運動後,一位德國軍官準備將作為人質的三兄弟行刑。他們的老母親跪在他腳邊,懇求他放過一個兒子。他同意了,但條件是得由她自己選擇哪一個。她選擇了大兒子,因為他有一個家庭要照顧。可是她的選擇等同於為其他兩個兒子宣判了死刑,而這,正是德國軍官想要的。
4)一群被遣返的女人,包括我們的一位同誌,途徑瑞士被遣送回法國。在進入瑞士國境後,她們看到一場喪禮。這場儀式使她們爆發出一陣歇斯底裏的笑聲:「這兒是這樣對待死人的啊」,她們說道。
我選擇這四個故事是因為在回答「人類危機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時,它們比一個簡單的「是」蘊含更多。故事中的人所呈現的答案,和我要回答的一樣:是的,人類危機是存在的。因為當今世界,我們帶著冷漠的態度、假惺惺的友好、研究的好奇心,或毫無反應的態度來看待人的被害和受虐。是的,人類危機是存在的。因為致人死地本應讓人覺得恐怖或羞恥;因為人的苦難被視為一種無聊的義務,和為車子加油、排隊買一盎司黃油差不多。
把矛頭指向希特勒是簡單的,並認為既然毒蛇已死,它的毒液也已消失。但我們清楚知道,毒液並沒有消失,它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看看國家、政黨、個人之間繼續彼此仇視就可以知道。我一向認為,一個國家對其叛徒和英雄都具有責任;文明也一樣,尤其是白人的文明,對墮落和成就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樣看來,我們都對希特勒主義負有責任,所以理應努力弄清這個將歐洲毀容的可怕的魔鬼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借助我所說的四個故事,讓我們來羅列這場危機最明顯的一些症狀:
1)
第一個症狀是恐懼的崛起。這是價值腐壞所導致的:評定人或曆史力量的並非尊嚴,而是成敗。當下的危機無可避免,因為西方沒有人對即將到來的未來有所把握;相反地,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憂慮,他們會被曆史以某種形式碾為塵埃。為了拯救可憐的人類,使這個現代的約伯(原本很幸福,卻被撒旦剝奪了一切的一位先知)不至於死於自己的傷口和糞土,首先應當卸下恐懼和焦慮的負擔,這樣才能重拾思考的自由,以解決現代良知所麵對的所有問題。
2)
這場危機還源於說服的不可能性。人要真正活著,必須相信彼此之間有某種共通點,某種讓把他們維係在一起的東西。如果他待人以善,他也期待善意的回應。但我們發現有些人是無法被說服的。集中營裏的囚犯不可能說服正在毆打他的德國黨衛軍,他不應該這麽做。剛才提到的那位希臘母親也不能說服德國軍官,他沒有強迫她心碎的權力。黨衛軍和德國軍官已經無法代表人或人類,而是一種本能,一種上升到思想或理論的狀態。激情,即使是致命的激情,也優於這種本能。因為激情有其持續時限。而另一種激情,來自另一個有血有肉的心靈的哭喊,是可以取代它的。剛剛撕裂了他人的耳朵又去予以慰問的人並沒有激情。他隻是一則數學公式,無法被克止,也無法與之辯解。
3)
這場危機還源自真實被印刷物取代,即,日益滋長的官僚主義。今天的人,在自己和自然之間設置了更多的道具,用抽象和複雜將人孤立起來。麵包短缺時,就出現了麵包票。法國人民每天隻能吸收一千兩百卡路裏,卻要用到六張不同的表格,每張有上百種票。這種官僚主義在各處擴張著。為了從法國來到美國,我在兩國都要用到許多文件,多到足以讓我為今天的演講印發足夠多的稿件,以至於我本人都用不著來了。那麽多文件、辦事機構、行政官員造就了一個人情味消失不見的世界。若想與他人接觸,必須首先穿越由所謂「規矩」所形成的一個迷宮。那位對著他親手撕裂了的耳朵說出安慰的話的德國軍官,認為這並無不妥,因為撕耳朵是他的職責之一,怎麽可能是錯的呢?在某些地方,人不再死亡、不再相愛、不再殺人——他們都隻是被召喚。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優秀組織」。
4)
這個危機還源於用政治的人取代真實的人。激情不再是私有的,而是集體的,即抽象的激情。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政治都變得無法避免。尊重或保護一位母親不受折磨是次要的,教義的勝利才至關緊要。人類的受難不再被視為醜聞,僅僅是個變量,昭示著一個無法計算的可怕的總和。
5)
顯然,這些不同症狀可被總結為某種對效率和抽象主義的崇拜。這就是為什麽今天的歐洲人隻擁有孤獨和沉默。他們無法通過溝通來分享價值,又由於他們無法受到基於那些價值的相互尊重的保護,他們隻能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中選擇。
二
這就是我同代的男人和女人所理解的。這就是他們曾經和至今仍麵對著的危機。我們曾嚐試用已有的價值來解決這個危機,然而唯一的價值就是生活的荒誕性。在這種精神狀況下,戰爭和恐怖來到我們麵前。沒有安慰,沒有確信。我們隻知道不可以屈服於正在占據歐洲四角的野蠻武力,但卻不知道如何將我們的抵抗合理化。即使是我們之中最聰慧之人,也找不到既可以反抗恐怖,又可以為殺戮正名的原則。
如果人們什麽也不相信,如果什麽都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價值可以被確認,那麽一切都是被允許的,一切都變得不重要。因此,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惡。希特勒既沒錯,也不是對的。有的人把幾百萬無辜的人扔進焚燒爐,有的人則全力拯救麻風病人;有的人撕裂他人的一隻耳朵,卻對著另一隻說出安慰的話。有的人能在剛被折磨完的人麵前,把房間收拾幹淨。有的人向死者致敬,有的人則把他們扔進垃圾桶。這些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認為一切都沒有意義,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勝者即正義。當下那些聰明的懷疑論者就宣稱如果恰恰是希特勒贏了這場戰爭,曆史將會賦予他榮譽,將他端坐著的殘暴的王座神化。而在可預料的將來,曆史甚至會把希特勒本身神化,為恐怖和屠殺辯護。就如現在我們宣稱「一切都沒有意義」也是在為恐怖和屠殺辯護。
事實上,我們當中的一些人的確相信,如果缺少更高層次的價值,人們隻能相信曆史是具有意義的。很多時候,他們的確表現得如同他們信仰的那樣。他們說這場戰爭是必要的,因為它會清算民族主義的時代,為帝製讓位於一個大同的社會、人間的天堂做好準備——不管是否涉及鬥爭。基於這種思路,他們得出和我們一樣的結論: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曆史有意義,那麽這種意義必須能被闡明,否則它什麽也不是。這些人的所想和所為,讓人以為曆史是某種超越性的辯證,人類正朝著一個確定的目標前進。他們按照黑格爾那可憎的原則來思想和行事:人類是由曆史所造就的,曆史卻不是由人類所造就。事實上,當今政治和道德的現實主義衍生於激進的曆史哲學。這種哲學認為全人類都在理性地朝著一個確定的宇宙前進,虛無主義已經讓位給一種絕對理性主義。本質上,兩者是一致的:如果曆史真是由一種超然和不可避免的邏輯所決定的話,如果這種德國哲學的假設為真——封建主義必然推翻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必然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必然推翻民族主義,並最終形成大同社會,那麽,支持這一進程實現的一切都是好的,曆史上的成功等同於絕對真理。由於這一切隻能通過戰爭、陰謀、對個人或集體的屠殺來達成,那麽行為的評價標準不再是善與惡,而是效率。
因此,我們這代人在當今世界正麵臨著一種雙重的誘惑:要麽認為什麽都不是真的,要麽認為不可避免的曆史力量才是真理。許多人屈服於這兩種誘惑的其中一種。也正因此,世界被有權力的人所統治,最終被恐怖主宰。如果沒有是非善惡,如果唯一的價值標準是效率,那麽唯一準則就是效率,強大的就是好的。世界不再按正義與非正義來劃分,而是分為主人與奴隸。因為他奴役他人,所以他是對的。公寓管家是對的,受刑者是錯的。下令施刑的德國軍官、施刑的人、掘墓的德國黨衛軍官,成為這個新世界裏有理的一方。看看你們周圍,是不是的確如此?我們被置於暴力的節點中,感到窒息。在每個國家,在全世界,懷疑、不滿、貪婪、和權力的崛起,正催生出一個昏暗、絕望的宇宙。在那裏,每個人都被迫局限在「現實」之中生活,而「未來」則會引起焦慮;每個人被迫相信抽象的力量,被追求效率的生活殘害而變得殘忍,被剝奪了自然的真理、思想的娛樂和最簡單的幸福。也許你們幸運的美國公民們看不到、又或者看不清這些,然而我所說的那些人已經經曆了好些年。他們在身體裏、在他們所愛的人眼中,捕捉到這一惡魔的存在。從他們受創的心靈深處迸發出一股可怕的反抗衝動,意欲掃除一切。太多殘酷的畫麵仍然縈繞心頭,使他們相信反抗並不容易。但同時,他們太深刻地感受到這些年的恐懼,無法忍受它們再繼續下去。問題這才真正開始。
三
如果這場危機的特征是權力的意誌、恐怖、由政治和曆史人物取代真實的人、抽象和曆史的必然性支配一切、以及沒有盡頭的孤獨,那麽為了戰勝這場危機,我們就應該改變這些。然而,我們這一代人麵對著如此巨大的難題,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確信。其實,我們應從這種否定中獲取戰鬥的力量。有人對我們說,你們應該信仰上帝、信仰柏拉圖、信仰馬克思,可這是徒勞的,我們並沒有信仰。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是否接受這樣一個世界:要麽成為受害者,要麽成為加害者。但我們兩者都不接受。因為在心靈深處,我們了解這種區別本身就是虛設。最終隻有受害者,因為殺害與被殺害,結局都是一樣的。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會承受同樣的失敗之痛。問題不再是接受或拒絕這種形勢、這個世界,而是知道該用何種理由來反對他們。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在這場反抗邪惡的鬥爭中尋找理由。我們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戰鬥,而是為了人類共有的某種東西。
為什麽這麽說呢?
在一個價值被剝離了的世界,在我們棲息著的心靈沙漠中,反抗可以昭示什麽呢?反抗使我們成為說「不」的人,然而同時,我們也是一些說「是」的人。我們對這個世界、對它根本的荒誕性、對威脅我們的抽象、對在我們四周建立起來的死亡文明說「不」。我們用說「不」來宣布,這一切已經持續太久了,有一條底線是不可逾越的。但同時我們肯定處於底線以內的一切。我們內心在拒絕殺戮、受苦,拒絕長久的侮辱。當然,有一個矛盾曾使我們猶豫。我們以為這世界的存在和掙紮是無意義的。然而事實上,我們卻在抵抗德國。我在抵抗運動中認識的一些法國人,在偷運宣傳材料的火車上讀著蒙田的著作。他們證明——至少在我們國家——可以在理解懷疑主義的同時懷有榮譽感。而我們每個人都在生活著、希望著、鬥爭著的事實,也在肯定著某種東西。
但這「某種東西」是否具有普遍價值,能否超越個人主觀性,成為大眾的行為準則呢?答案很簡單。我所說的那些人,隨時準備為他們投身的這場反抗鬥爭獻出生命。他們的死將證明他們為其犧牲的真理是高於他們個人的存在、超越他們個人的命運的。當我們的競爭對手在為命運的悲觀性辯護、質疑這種價值是否普世,當人在自己的管家麵前受刑,當年輕人被淩辱,當母親被迫宣判自己孩子的死刑,當正義被當作豬一樣被埋葬時,這些人的反抗為某些曾被否定的東西正名,而這並不隻屬於他們,而是人類可以團結起來去爭取的共善。
是的,這是那些可怕的年月所帶來的巨大教訓。一位布拉格大學生所遭受的侮辱,會影響一位巴黎郊區的工人;灑在東歐一條河岸上的鮮血,能激起來自得克薩斯州的一位農民把自己的血灑在他踏足沒多久的阿爾登森林(位於德國)。盡管這一切是荒誕瘋狂的,幾乎不可能被想象。但正是透過這種荒誕,我們意識到在這場共同的災難中,我們共同的尊嚴正受到危害。我們應當去維護和維係一個人類的共同體。懂得這一點,我們才知道該如何行動,才會明白即使道德完全荒蕪,我們也能找到足夠的價值,指導我們的行為。一旦人們明白,真理在於溝通和彼此認可對方的尊嚴,就會明白對話正是我們應該去追求的。
而要使對話得以延續,人必須獲得自由。因為主人和奴隸沒有共同之處,對一個奴隸,是無法溝通的。是的,束縛等同於讓對方沉默,這是最可怕的沉默。要使對話得以延續,我們應當肅清非正義,因為受壓迫的人和從壓迫中獲益的人是無法溝通的。要使對話得以延續,我們也應當消除暴力和謊言,因為說謊者將別人拒之門外,他會用施暴和約束將沉默強加於人。否定的衝動是我們反抗的開始。我們要求得到平等和真摯。
是的,我們需要通過對話來反抗這個殺戮的世界。這正是今後我們要堅信的。如果想保護自身免受殺戮,我們必須保持對話。我們需要抵抗不公正、抵抗奴隸製、抵抗恐怖,因為正是這三大災難使人類變得沉默、分裂,使人類相互視而不見,使他們無法發現,將他們從絕望的世界中拯救出來的唯一的價值——與命運相抗爭的人們之間的友愛。在這漫漫長夜的盡頭,我們最終明白,在這被危機撕裂的世界中我們所應該做的是:
1)
我們應當直言不諱,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每當我們讚許某些思想,等同於殺害了千百萬人。我們並不覺得,因為我們是凶手;我們是凶手,正是因為我們是這麽想的。因此即使不殺害,我們也會成為凶手。因此,我們大家多少都成了凶手。頭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摒棄宿命論的觀點。
2)
我們應當把世界從統治著當下、阻止思考進行的恐怖中解救出來。據我所知,聯合國正在這個城市裏舉行一個重要的會議,我們或可以建議這個全球性組織的第一份文件,應以紐倫堡審判為鑒,嚴肅地宣告廢除遍布全球的死刑。
3)
政治應盡可能被置於一個它應處的範疇內——一個次要的範疇。我們不需要福音書或政治、道德的教理書來粉飾世界。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恰恰在於政治試圖為我們提供一本教理書和一套完整的哲學,有時甚至指定關於愛的方式。但政治的角色是維持秩序,而不是規範我們的內心。對我來說,我不清楚是否有絕對真理的存在。如果有的話,也與政治秩序無關。絕對真理並不取決於集體,而在於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思考絕對真理的心靈空間。而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應予以我們這種自由。我們的生命,毫無疑問是他人給予的,有必要的話,可以將生命獻出;但我們的死亡隻屬於自己。這就是我對自由的定義。
4)
第四件事,是要從否定中尋找和創造能夠調和消極思想、能夠激勵樂觀行為的正麵價值。這是哲學家的事。而第五件事是要明白,這種態度意味著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普遍主義,使心懷善意的人得以共聚。若想遠離孤獨,我們必須交談,但交談必須是坦率的。無論如何不撒謊,隻說所知為真之事。但隻有在一個基於普世共同價值的世界中,我們才有可能談論真實。孰對孰錯,並非由希特勒來裁定。不管是現在或以後,任何人都沒有權力認定他的真理最正確的,可以強加於其他人。隻有被共同認可的良知才能實現這一宏願,而我們必須去發現支撐這一共同良知的價值。我們最終要贏得的自由,是不說謊的自由。隻有這樣,才能找到生存或死亡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立場,我們走了一條遠路,但人類的曆史說到底是人類的錯誤史,而不是真理史。也許真理就像幸福一樣,是簡單而沒有曆史的。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得到解決了呢?當然不是。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或更理性。我們尚未終結荒誕。但至少我們有一個驅動我們改變行為的理由了,這在不久前還是缺失的。沒有人類的世界,是絕望的。但人類存在在世界上,帶著他們的熱情和夢想,他們的族群。我們在歐洲的一些人,把對於世界的悲觀主義和對於人類的深刻的樂觀主義結合了起來。我們無法假裝逃避曆史,因為我們身處曆史之中。隻有在曆史的競技場上戰鬥,才能將人類從並不屬於他們的曆史中拯救出來。我們發掘過去的文明,既不拒絕曆史,也不再受曆史的奴役。人有對他人應盡的義務,也應同時擁有作為他個人的思考的時間、愉悅和幸福,作為平衡。
我想大膽提出,我們應始終拒絕崇拜任何當下的事件、事實、財富、權力和曆史。我們應正視人類的現狀,而我們知道現狀是怎樣的。一車車的屍體和幾世紀的曆史,隻帶來人類命運的微小改變。這是規律。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有好多年,年輕人掉的腦袋像麥穗一樣多。大革命點燃了人們心中的熱情和恐懼,最終在十九世紀初,世襲君主製被君主立憲製所取代。我們,二十世紀的法國人,實在太了解這些可怕的規律。需要戰爭、占領、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囚犯、一個被悲痛摧毀的歐洲,才使我們中的一些人領悟到能夠稍微減輕失望感的兩三事。對於我們這種境遇,樂觀主義似乎是可恥的。我們知道,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已經死了,因為他們選擇了死亡。而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應該意識到我們之所以還活著,是因為我們做得比其他人要少。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繼續生活在矛盾之中。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這代人在矛盾之中納入了人類的巨大希望。之前提及,要談談法國人的感性,那麽也許你們記住以下這些就夠了:今天,在法國和歐洲,有這麽一代人,他們認為寄信於人類的人都是瘋子,但提前感到絕望的都是懦夫。他們拒絕絕對的解釋和政治哲學的統領,而是努力透過有血有肉的人,以及他們對自由的努力來獲得確信。他們不相信可以實現普世的幸福或滿足,但相信人類的痛苦是可以減少的。正因為世界在本質上是不幸的,我們就應該創造幸福。因為正義缺失,就應該為正義而努力;因為世界是荒謬的,就應該提供某種意義。
最終,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我們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應當謙遜,恪守崗位,做好本職之事。它意味著我們應當在黨派和政府之外創立一些共同體和思想,以促進超越國界的對話。這些共同體的成員通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言談來證明,世界不應由警察、軍隊和金錢主宰,而應成為一個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人們勤奮工作、愉快思考。
我們應當將我們的努力、反思,甚至犧牲,往這個目標引導。古希臘的崩潰是由蘇格拉底被刺開始的。這些年在歐洲,我們殺死了許許多多的蘇格拉底。這是一個信號。它昭示了隻有蘇格拉底式的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思想,才能對建立在殺戮之上的文明構成真正的威脅。隻有這種思維方式能修複這個世界。而任何依賴權力和統治的作為——無論多麽令人欽佩,都隻會更深刻地殘害人類。以上,就是法國和歐洲正在經曆的微不足道的革命。
結語
也許你們會感到驚訝,一位被正式邀請到美國來的法國作家,既沒有向你們描繪一幅有關他的國家的田園牧歌式的圖景,也沒有所謂「宣傳」的意願。但如果仔細思考一下我剛才的闡述,就會理解為什麽了。宣傳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在人們心中激起他們並未擁有的感受。但那些與我們有相同經曆的法國人,並沒有要求他們被憐憫或被愛。他們認為困擾他們的唯一的國家問題,並不取決於世人的看法。這五年來,對我們來講重要的是是否能挽救尊嚴——一旦戰爭結束,是否能擁有言論自由。這項權力不期望由任何人所給予,需要我們自己去爭取。這原本並不容易,但最終如果我們得到這種權力,那是因為我們——也隻有我們——知道究竟做出了多大犧牲。
我們並沒有教導他人的權力。但被鞭笞太久的人的沉默是羞恥的。除此之外,我想請你們相信,我們隻會守住自己的位置。也許正像有人所說,曆史的後五十年將由法國以外的國家來譜寫。關於這一點,我沒有看法。我隻知道一個在二十五年前失去一百六十二萬人口、並剛剛失去數十萬誌願兵的國家,已經用盡力氣。這是事實。而世界輿論—不管是關心或輕視—都不會改變這一事實。因此,索取同情或嚐試說服都是荒唐的。然而,闡明這場世界危機源自於對特權和權力的爭奪,並非荒唐的事。
作為今晚演講的總結,在最後,我個人想說的是:每當我們用權力來評價法國或其他國家,又或任何問題,我們就會離人類的分崩離析更進一步,就會加深對統治權的渴望,並最終導致殺戮的合法化。思想決定行動。那些宣稱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強大即偉大的人,對於今夭滿目瘡痍的歐洲的種種可怕罪行負有絕對的責任。
我想,我已經很清楚地表達了我應對你們說的話。我的責任是忠實地反映我在歐洲的同誌們的聲音,以防你們對他們作出草率的評價。他們不充當任何人的審判者,除了殺人犯之外。他們用充滿希望和確信的目光看待所有國家,並且堅信每個國家都能找到屬於它自己的人類真理。
對於今晚來到這裏的美國年輕人,我還想補充幾句。我所談及的那些法國人非常尊重你們的人道主義以及你們擁有的自由和幸福。這些在廣大美國人民臉上清晰可見。是的,他們對你們的期望,與他們對所有正直的人的期望一樣——為建立世人之間的對話而真摯地投入。從遠處看,我們的鬥爭、希望和要求似乎讓人不解或是徒勞的。的確,如果通往智慧和真理的道路真的存在,這些人並沒有選擇最直接或最簡單的那條。那是因為無論世界還是曆史,從未提供任何直接、簡單的路。現狀無法給予的,他們就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也許他們會失敗。但我相信如果他們會失敗,這個世界亦然。在依然被暴力和深植的仇恨的毒害的歐洲,在被恐懼撕扯得支離破碎的世界上,他們會努力挽救在人類身上殘存的人性。這是他們唯一的願望。這些努力如果在法國能夠收到一些效果,如果今晚我能讓你們了解到鼓舞著法國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即使隻有那麽一點點——將會是唯一的安慰,以及我個人小小的自豪。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超前預見性!加繆1946美國演講:人類的危機